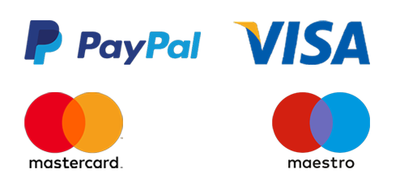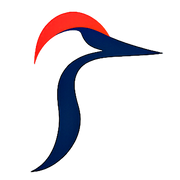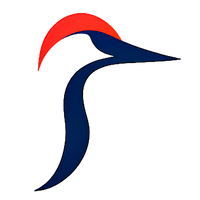泉州簪花记:在海丝古港,簪一束山海繁花
分享
从泉州站出来,湿热的海风裹着淡淡的茉莉香扑面而来,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 “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 的古城,用最温柔的气息接住了我的脚步。此行最心心念念的,便是去蟳埔村赴一场 “簪花之约”—— 那抹绽放在闽南女子鬓间的艳色,早已在我心中种草了许久。
坐公交往蟳埔村去,沿途的景致渐渐褪去都市的喧嚣。红砖古厝的燕尾脊刺破天际,墙上的 “出砖入石” 工艺像拼图般精致,偶尔能瞥见墙根下坐着摇蒲扇的阿嬷,鬓边若隐若现的碎花,让我愈发期待接下来的体验。村口的牌坊上刻着 “蟳埔” 二字,不远处的滩涂里,几艘渔船斜斜地搁浅着,渔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,像是撒在滩涂上的星子。
顺着导航找到一家口碑不错的花屋,木门 “吱呀” 一声推开,满室花香瞬间将人包裹。竹篮里码着各色鲜花:茉莉雪白、素馨嫩黄、三角梅艳红,还有些叫不上名字的小花,花瓣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,鲜活得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声响。“姑娘是来簪花的吧?快坐!” 花屋的林阿嬷笑着迎上来,她的手上戴着银镯子,说话时镯子轻轻碰撞,叮当作响。
阿嬷先取来木梳,细细梳理我的长发。她的手指粗糙却温暖,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薄茧,梳齿划过发丝时格外轻柔。“我们蟳埔女梳头发有讲究,要盘成‘田螺髻’,像不像海里的田螺?” 阿嬷一边说,一边灵巧地将头发拧成一股,一圈圈盘在脑后,最后用红绳固定住。接着,她从竹篮里取出花束,先将素馨花绕着发髻缠成圈,再把茉莉和三角梅一簇簇插在两侧,“以前啊,渔女们戴花是为了祈求出海平安,现在日子好了,戴花就是图个喜庆,让日子像花一样热闹。”
当阿嬷递来镜子时,我竟有些恍惚。镜中的自己,长发被繁花簇拥,雪白的茉莉贴着耳畔,艳红的三角梅垂在肩头,海风一吹,花瓣轻轻颤动,连带着整个人都多了几分闽南女子的温婉。阿嬷又拿来一条蓝色的头巾,在我颈间打了个结:“这样更有我们蟳埔女的样子!”
戴着满头繁花走在村里的石板路上,成了最亮眼的 “风景”。路过一家卖海蛎煎的小摊,老板娘笑着招呼:“姑娘簪的花真好看,要不要来份海蛎煎?刚挖的海蛎,鲜得很!” 我坐下尝了一口,海蛎的鲜甜混着鸡蛋的香,蘸上甜辣酱,一口下去满是大海的味道。老板娘说,村里几乎每个女人都会簪花,从七八岁的小姑娘到七八十岁的阿嬷,哪怕是去菜市场买菜,也要在鬓边别上两朵,“这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,不能丢。”
沿着小巷往海边走,遇见几位同样簪着花的阿姨在补渔网。她们的手指翻飞,麻线在渔网的破洞处穿梭,鬓边的鲜花随着动作轻轻晃动,与身后的红砖古厝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民俗画。我忍不住上前搭话,一位阿姨笑着说:“以前男人出海捕鱼,我们就在家补网、簪花,等他们回来。现在孩子们都去城里了,但我们还是习惯簪花,这花啊,就像我们蟳埔人的根。”
走到海边时,夕阳正缓缓落下,将海面染成了一片金红。我坐在礁石上,看着远处的渔船渐渐归港,海风吹拂着鬓边的鲜花,茉莉的清香与海水的咸涩交织在一起。忽然想起在泉州城里看到的开元寺东西塔,想起清净寺的阿拉伯式穹顶,想起西街的古早味小吃 —— 这座古城,既有海丝文明的厚重,又有市井生活的鲜活,而蟳埔村的簪花,正是这份鲜活里最动人的一笔。
离开蟳埔村时,我小心翼翼地护住鬓边的花。阿嬷说,这些花能开两三天,我想把这份来自泉州的浪漫带回家,让它提醒我,在这座海丝古港,曾有一场与山海繁花的温柔邂逅。而泉州的故事,也像这鬓边的鲜花一样,在我心中缓缓绽放,久久不散。